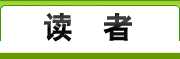-口述/郑铭昊 整理/千北
罗布泊曾经是水乡泽国,在许多的年月之前。然后它是突然消失的,从地球上消失了,只留下一个“耳朵”形状的盐碱地痕。不知道这个由卫星探测出来的地表上最大面积的“耳朵”,它在倾听着什么,又在昭示着什么?
寻找原音的女孩
2003年3月1日,我回到武汉某地质研究所上班。其实2001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就已正式分配到这里,但之后便随勘查队去了湖北陨西山区采集和考察岩石地貌,这一去就是一年半。
上班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,我在办公室加班。我办公桌的位置正好在窗边,初春的阳光照在我的后背上,身体便跟蛰伏了一冬的枝条似的,积蓄那温暖的力量绽放新绿。
这时,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。我一愣,回过神来,不知是谁将电话打到我办公桌的分机上了。犹豫了一下,我接了电话。
一个女孩的声音几乎是脱口而出:“柯伟?!”还来不及反应,我先“嗯”了一声,觉得不妥,想再解释时,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字字急切了,响在耳边:“柯伟,是你吗?真的是你吗?可是,总机接线的录音电话里已经不是你的声音了,你说话啊,让我再听听你的声音。你告诉我,我要上哪里才找得到你的声音?”
然后是一阵沉默。我莫名地感到窒息,仿佛连呼吸的声音都停止了。电话里只有噪音在吱吱地响,可是我听得见那女孩无声哭泣的声音。
电话挂断了。
第二天下午我依旧在办公室加班,但明显有些心神不宁,偶尔看着桌上的电话,似乎有所期待。可当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时,我还是被吓了一跳。打来电话的果然还是昨天那个女孩,她说:“你好。”
我镇定了一下,习惯性地“嗯”了一声,然后说:“你好,我是郑铭昊。”女孩的声音是舒缓的:“我叫蓝云。对不起,昨天是我打的电话,打扰你了。”我往椅背上靠了靠,让阳光可以覆盖我的整个身体:“没关系。”
蓝云突然说:“你的分机号码是131吧,我以前常打这个电话,所以昨天显得有些冒失了。”沉默片刻之后她突然说,“你的办公桌还是靠窗吗?阳光很好吧,晒得身上暖融融的。再次向你道歉,再见。”
蓝云又一次从电话那端消失了。她是谁?她原本要给谁打电话?柯伟又是谁?
我让总机室的接线小姐帮我查找蓝云的电话号码。她在总机电话上一阵翻查,然后抄了一串号码给我,那应该就是蓝云的手机。
就要走出总机室,我突然回头:“嗯,你知道柯伟是谁吗?”
小姑娘一愣,然后说:“柯伟,是啊,他曾经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,分机号码是——131。”
我继续问:“是不是公司原来的接线录音是他说的?”
小姑娘很诧异:“你怎么知道?他是北方人,声音很好听,所以原先总机电话是请他录的音。不过,自从他走了之后我就重新录了一遍。”
我微微沉吟:“嗯,当时他录音的带子还在吗?”
小姑娘说:“我找找吧。嗯,我发现你俩都喜欢在说话之前加一个‘嗯’呢。”
我终于知道了,柯伟是我曾经的同事。用“曾经”两个字,是因为柯伟已经去世了,那是2002年底的事情了,因为车祸。
我还知道,柯伟在总机电话里录音的原文是:“你好,这里是总机,请拨分机号,查号请拨零。”
嫁给我是因为原音重现吗
我给蓝云打电话:“你好,我是柯伟的同事,嗯,你曾经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的。今天我在帮忙整理总机室资料时发现了一盒录音带,是柯伟原先录下的声音。我们留着这盒录音带也没用,我想,也许你愿意留作纪念。”
蓝云答应了,她在武汉广场一家外资企业工作,我们约在附近咖啡屋见面。
她很年轻,和这个城市里所有白领女孩一样,化精致的妆,温柔地说话,只是彬彬有礼中带些冷淡,想象不出她尖叫或是大声笑的模样。还有,她手里的手机是最新式样的,可以录音和拍照的那种。
然而我分明看得见她眼眸里与众不同的东西,一些隐藏得深刻的狂野,或是地质学上称为“荒原”的悲凉。也许因为她曾经爱过一个地质队员吧,我这样解释看到她第一眼时内心所产生的熟悉感。
我将录音带递给蓝云,她低眉叹息:“谢谢你这么细心。你可以理解吧?柯伟走了之后,他的电话号码我一直舍不得删掉,偶尔我会打那个电话,以为还能够听到他的声音,听他说‘你好,这里是总机’。”蓝云在复述总机接线录音时声音里带种奇异的颤音,“没想到那天我打去电话,碰巧你现在也用131的分机号……”
我一直期待蓝云再次给我打来电话。一周后,我终于在手机屏幕上看见了“蓝云”两个字。
蓝云说,她这几天每天晚上都会反复地听柯伟的原音,她要感谢我让原音重现了。
我不可自抑地爱上了蓝云,爱她微蹙的眉,爱她凝神听我说话的神情,爱她为情所伤的孤苦。我发誓要让她重新得到快乐和幸福,要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和婚姻。
2004年1月,蓝云答应了我的求婚。
新婚前夜,蓝云将她的东西都搬到我的小屋里。除了衣物、化妆品、书籍、CD之外,还有一台老式的录音机,当然还有那盒录音带。
那是我第一次和蓝云一起听那盒录音带。
磁头空转的声音,仿佛科幻电影里的时光机轰隆隆,做出发前的准备。我悄悄看蓝云,她的眼睛闭上了,我的心底一声叹息,也许她的思绪在穿梭吧,如果可以飞就飞起来吧,飞向天空的尽头,时光的尽头。
然后一段很长时间的空转,是柯伟当年在房间里录制的吧,哑哑的,听得见磁带与磁头的磨合声;哧哧的,听得见呼吸在空气里流转。突然柯伟的声音响了起来,响在整洁的房间里。柯伟说:“你好,这里是总机,请拨分机号,查号请拨零。”
那个声音,那个从来只是飘荡在心里的声音,突然就立体了,凸现了,真实地复原了。那个声音从过去的时空里返回,回到现实,回到蓝云耳畔,回到我和蓝云的生活里。
我没有看蓝云,但我知道她正在流泪。
我递给她一块柔软的纸巾,想开口安慰她什么。我说:“嗯。”那样地,长长地,叹息一样地说“嗯”。我还没想好该说什么,正接过纸巾的蓝云指尖一颤,她的手滑过纸巾,握住了我的手。她的小手冰凉。
蓝云看着我的眼睛说:“谢谢你。你答应我,我们的婚姻一定要幸福,好吗?”
谎言和诺言有时是相同的
2004年6月之前,我们的新婚生活是幸福的,只是蓝云依然不太多说话,她喜欢听我说。有时我们一星期面对面说的话,还比不上她每天在QQ上和我说的话多。
我知道蓝云心里有些隐痛,但有时爱一个人就是前世欠她的,包容她并接受她的所有
我知道蓝云也在努力经营我们的婚姻,因为她还是愿意与我交谈的,愿意告诉我她的想法,当然只是在QQ上,用手指用电脑用网络用听不见声音的文字。
QQ聊天的时候蓝云是活泼的可爱的,轻松的自然的。可能那才是本来模样的她吧。
两个人独处的时候,蓝云就沉默了。
蓝云最喜欢的游戏是用手机录下一些声音的片断。她热爱声音的复制,并希望尽可能地逼真地还原。她爱这个游戏,并乐此不疲。
有天夜里,万籁俱静,我从梦里醒来,张开手臂往身边一拥,蓝云不在。卫生间有声音,可是好半天她还没有回来。我躺不住了,起身去卫生间,从半掩的门里,我看见蓝云正拧开水龙头,看一滴一滴的水,花一样绽放然后碎裂在洁白瓷砖上。她在录水滴的声音。
她在录这寂寞的声音?
甚至有一次,我无意中发现蓝云瞒着我做一件事。那是6月的一天,蓝云正在卫生间洗澡,她的手机响了,我替她接了手机后,无意中对她功能齐全的手机产生了好奇。我发现她在声音录制一栏里复制了许多“个人文档”,我随便播放其中一段,好像是下雨的声音。再播放,是我回家敲门并在门口大声喊“云儿,我回来了”的声音。再然后,我竟然在蓝云的手机里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声,那是战栗的声音,然后是我呢喃的话语,我在说“嗯”或是在说“我爱你”。
身边没有人,但是我的脸却刷地红了,几乎是带些害怕地丢下了蓝云的手机。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,无论手头正在做什么事,但稍不留神我就走神了,耳边是自己快乐呻吟的颤音。
有风的日子,她录下风声。下雨的日子,她录下雨声。无风无雨的日子,蓝云喜欢静静坐在卧室的窗前,看光影重叠,看云聚云散,那样的时候,我在她的身后,我知道时光正像青苔一样悄悄覆盖她的心。但是为什么,她要录下欢爱正浓时我的声音?
蓝云从卫生间出来后,从沙发上拾起我丢下的手机,深深地看着我,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什么。
那一夜,我久久无法入眠。我知道,身边的蓝云和我一样。只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。
第二天上班后,我和往常一样打开电脑,QQ自动登陆。
蓝云的头像在闪烁,她对我“说”的第一句话是:“在五笔里,诺言和谎言是相同的笔画,都是YAYY。”
蓝云说:“对不起,我是无意中知道你的秘密的。”
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发现我的秘密的。她说的那天的情形我也记得很清楚。那天是2003年12月31日,我的父母从老家来武汉看我,同时他们也想见一见蓝云。那天蓝云正好感冒,我便独自去车站接站。
蓝云的叙述让那一幕历历在目:“等待有些无聊,我突然想听听音乐,于是我在你的抽屉里翻出了一盘磁带。磁带是你大学时最爱的英文歌曲吧,是卡朋特的《昔日重现》。封面已经泛着浅浅黄色了,我按下播放键。我没有听到歌声,却是些被撕碎的声音,断断续续的,有时是歌声,有时是噪音,还有时是谁在一遍遍反复地说‘你好,这里是总机’。最后我听到一个似乎熟悉的声音,我听出来了,是你们研究所那个接线员女孩的声音。我清楚地记得,因为这个声音替代了柯伟曾经的录音。我听见那个女孩的声音出现在磁带里:‘啊,你学得真像啊,柯伟就是这么说话的。你们都是北方人,音质也像,哪怕是我可能也分辨不出来呢。何况你还可以说,磁带转录的声音总不可能完全复原的。’然后是你的声音,你说:‘她不会问我的,我想她一定不会去追问到底这是谁的声音,她只是需要一些声音,一些传递温暖和关爱的声音,陪伴她。’”
蓝云最后在QQ上告诉我:“你知道吗?我是在知道你骗了我之后,决定嫁给你的。”
我长久地沉默着,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如果说这是谎言的话,我承认。谎言是因为爱。
我在说那些谎言的时候,也是在说着爱的诺言。
难道蓝云不能明白不能体会吗?
就在那一天,我们研究所所属的大学学生会与所领导联系,希望能够有位专业人员陪同他们的志愿者完成“罗布泊探险”活动。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当时我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,我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考和蓝云之间的关系,罗布泊是个安静的地方,正适合我当时的心境。
我什么都没有说,只是告诉蓝云我要离开一个月,前往罗布泊。
其实心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横亘着,我只想问她:“你嫁给我,是因为我与柯伟的声音相似吗?你录下我的那么多声音,包括床上的声音,是在臆想着将那当作是柯伟的声音吗?”
然而,我问不出口。
行走在罗布泊
2004年7月中旬,我和一群大学生探险队员来到了罗布泊。
罗布泊原本是个湖泊,它曾经是面积约2400~3000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在古时正处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“丝绸之路”要塞之地,是繁华之地,是荒漠里的水乡。然
1972年7月,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罗布泊的照片上,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这只地球之耳是如何形成的?有无数的传说,其中有一种就是称它为“心灵之耳”,说心湖是属于一位徜徉爱情中的少女的,因为情人的远离和再无音讯,少女的心湖干涸了,最后变成了一只耳朵,伏在地面上,希望可以听到情人归来的脚步声。
我是研究地质地貌的专业人员,但我仍然被这个传说深深地打动了。
从武汉出发的那天早上,蓝云固执地将她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对换了,可是除了接听电话,我没有翻看那个手机。我不知道蓝云将那些录音删去了没有,也没有勇气去查看她的手机里还有什么秘密。
可是因为来到罗布泊,因为听到“心灵之耳”的传说,我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。如果将心灵比喻成罗布泊的话,它们同样是奇特的区域,可以是江南水乡,草长莺飞或是落英缤纷;也可能成为无人荒漠,除了盐碱地还是盐碱地,寸草不生。
罗布泊还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原成湖泊,只要有足够的雨量,只要有河流从天山南坡冲击下来,并沿河道的方向进入干湖盆。我站在罗布泊的荒原里,想象着有暴雨倾盆,想象着“耳朵”慢慢渗入雨水之中,消失自己,淹没自己,像是一颗心,快乐地被温言软语滋润,像是沉浸在爱的泽被之中。
就是在那一刻,我拿出了蓝云的手机。
手机没有讯号,然而我在手机里看见声音文档仅存了一个文件,文件名叫“说给郑铭昊听”。
我将手机贴在耳边,然后我听见了蓝云的声音,那么真切那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畔,这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听到蓝云对我说了那么多的话:
“在柯伟走后,在认识你之前,我一直生活在无边的后悔中。我总在想,我应该录下他的声音的,那是他的原音。所以我喜欢一次次拨打研究所的总机电话,当时那是他在世间仅存的声音了。我还想,我应该和他生一个孩子的,孩子是他的原音。可那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了。这些我都没来得及做到,我常责备自己,我该到哪里去寻找他的原音?直到我遇见了你。
是你带给了我那盒音带,是你让原音重现,虽然我知道那是假的。但我怎么能够认为那是假的呢?你的眼睛、你的声音分明是真的。因为爱,是真实的。”
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……
听爱的声音
8月20日,我带着学生们返回了武汉。
回家途中,我给蓝云打了一个电话,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回来了。”
蓝云去车站接我。远远地我向她举起手机,那里面贮存了许多声音,是我一路上录制的,我要播放给她听。
我在荒漠里独自伫立的声音,有风吹,有沙掠过。
我在火车上录下的铁轨轰隆声,像是急切的心跳声。
……
这些,都是我思念蓝云的声音。
因为蓝云在手机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录下你的声音,不是因为相似,不是在怀念旧爱,而是因为害怕。我一天比一天更新鲜地发现你的好,一天比一天更爱你,仅仅因为你是郑铭昊。越爱你越是害怕再次失去,我不愿再犯同样的错误,所以我拼命地录下你的声音,你任何时刻的声音,当然,我最沉迷的还是我们最亲密时的情话,这些,你能理解吗?我在爱你,我只是在记录爱的声音。”
我和蓝云仿佛重新在恋爱了,重新去了解和发现生活中每一个感动的细节,我们细心录下每一种关于爱的声音。
我喜欢吻她的耳朵,轻轻地用舌尖探测耳朵的形状,或是哈一小口暧昧的空气,酥软会遍及全身。
我喜欢咬她的耳垂,微微的疼与迷乱的情往往便结伴而来,那一刻远航的汽笛声从耳边呼啸而过。
我更喜欢在她的耳边诉说,有时清晰表述,有时含糊暧昧,我发现她耳朵上有个小粮仓,我喊她的昵称,讲温柔的情话,或是不成句不成词甚至没有一个字,只是些甜蜜的呢喃,尖锐的呻吟……
而所有这一切,我得到了同样的回应,爱的回应,声音的回应。
2005年3月初,蓝云满脸羞红地告诉我,我要当爸爸了。
无法形容那一刻内心的狂喜。
我去买来一个胎心监听仪,打开扩音装置,我们的孩子在子宫里快乐地游来游去的声音就清楚地响在小屋里了。“咕咕”,他在干什么?游泳?还是玩脐带?还是吹泡泡?
无论什么,都是爱在诉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