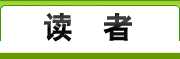我在台北的咖啡屋变成了女野人,我打那个男人。
我失去了风度吗?我令人侧目吗?我需要检讨吗?
不,我不后悔,因为这件事是在证明,我活着,有血有肉地活着。
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台湾东部的一个孤儿院里度过的,那段并不幸福的童年生活让我记忆犹新。
大概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,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孤儿,被送进了花莲一家孤儿院。那时花莲仍然是台湾最美的地方,但因为局势动荡,经济萧条,而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,孤儿院的条件很差。
我小时侯性格孤僻,与孤儿院的生活格格不入,但我必须学会乖,因为如果不乖,就要挨打。
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,叠被整床,刷牙洗脸,行动俨然是一个小军人,然后我与另外20个女孩们排成两列,进入餐厅共用早餐。我们的早餐是一碗清清的米粥,两片玉米饼或油条加咸菜,末了每个人还可以发一根小黄瓜或新鲜的西红柿,那都是我们自己的菜园子里种的,我们没有什么水果吃。
记得是某个星期六的早上,早餐之后我回到宿舍,看见舍管在追逐一只美丽的蝴蝶。要知道,台湾盛产蝴蝶,我们这所坐落在山区的小孤儿院,也常常会闯入蝴蝶。那仿佛是一只黄裳凤蝶,翅膀很大,颜色炫黄,美丽无比。她的身后还陆陆续续跟着几只小一点的蝴蝶,同样很美丽。
我小心地看着舍管捕捉这美丽的生灵,她从网里将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相继取出,然后用大头针穿过它们的头和翅膀,用针将它们固定在厚纸板上。
这是多么残酷的方式,她并不先杀它们,而是活活地把它们固定,让它们等死。
那次以后,我曾经独自走在矮树丛许多次,去寻找这些可爱的生灵。渐渐地,它们不再怕生,聚集在我的周围,有些胆大的蝴蝶还在我的头、脸和手上停留。我喜欢蝴蝶。
有一天下午,我终于忍不住,趁舍管不在时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。她一直喜欢收集蝴蝶制作标本,我看到了那些厚纸板上被大头针钉着的蝴蝶。有一只大概是刚刚被钉上,翅膀显然在动,我伸出手去碰它的翅膀,一枚大头针被我弄掉了。
我以为那只蝴蝶会开始振翅逃命,可是,它没有动。我小心翼翼得把另外一枚大头针也拔下,它还是没有动。当我把全部的大头针从它的身体上拿走后,它似乎哆嗦了一下,但是,它还是没有摊开翅膀,匍匐在纸板上,它不肯飞了。
后来的事情可想而知,舍管从菜园子回来后开始对我大骂。
我站在那里,默默地承受着舍管的辱骂,但是一句也不敢反驳。
最后,她拿起厚纸板打我的头,各种蝴蝶碎片散落下来,像下雪。
我在孤儿院一直呆到10岁,后来,被一对夫妻收养,离开花莲,去住台北。养父母对我管教很严格,也是动不动就打骂。但我在孤儿院已经学会了沉默,我按他们喜欢的去做,努力学习,拼命拿好成绩。后来,我进国中,考上大学。
就在我大学快要毕业那年,我的养父母在印尼旅游,遭遇海啸不幸去世。
我一度非常难过,少年失怙已经很悲惨,养父母也意外遇难,大学马上就要毕业,老老实实的乖女,怎样才能在千军万马闯关的台北找到工作?暑假时,我一个人呆在家里,那一年,台湾下很大的雨,我在家里做家务,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跑去开了门,没想到是和我做了很久邻居的润明。他满脸雨水,小心翼翼地对我说:“别太难过了。”我愣了愣:“还有什么事吗?”润明抹了一把脸,说:“没有什么事,我刚刚出门时看到你一个人在房间呆着,忽然就想告诉你这句话。”
我眼眶开始湿润,润明笑笑说: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,我可以帮你忙。”他发动机车,开走了。
我和润明有了一个平淡的开始。润明爱玩,动不动就和朋友出去。但他从来不带我去,因为我是“乖乖女,不会玩,没有意思”,我也觉得我更合适在家里,我喜欢当宅女,安安静静,与世无争。我不介意润明出去玩,毕竟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,喜欢的东西有所差别, 他没必要整天陪我,他也应该找点他的乐子。三年后,我们准备结婚。这个时候,我忽然被查出患了乳腺癌。我才23岁!起初,我和润明都不相信23岁的女生怎么可能会得乳腺癌,但是几家医院检查以后,事实证明,我真的很不幸,医生说肿块是恶性的,必须做手术,否则癌细胞扩散了,命都难保。
我平躺在医院的手术室。麻醉过后,绿袍的麻醉医生在用针刺我的胸,问我痛不痛。
我说:有一点痛。
医生隔了一分钟,又来刺我,问我痛不痛。
我说:还有一点点。
医生加大了麻醉药的剂量,又刺了几针,我感觉不到痛了。
这时他们开始做手术。
那次手术的经历,最让我难以忘记的不是我的左胸被切开,肿块被拿掉,皮肉被掀起、缝合。我无法忘记的是那根试探我是否还有痛觉的针。药麻痹了痛觉神经,但触觉神经还在,我清楚地记得每一针的位置,走向,和每一针的深度。它刺我,直到我习惯了那种刺,直到我说:我不痛了。
我觉得我很像童年时代的那只蝴蝶,还活着,但是,感觉不到痛了,不想再动了,也没有飞起来的欲望。
那一年,台湾的雨仍然很大,我和润明坐在咖啡馆里,他向我摊牌:“我确实在和别的女人好了,她怀了我的小孩,你,你能生吗,瞧你的身子。”我看着润明的眼睛,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浓黑,但是它却变的无耻。“我不能和一个没有胸部的女子结婚。”他看着我,带着怜悯和嫌弃说:“你多保重吧,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,我走了。”
我说:“你等等。”
在那一瞬间,我站了起来,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,是愤怒?是委屈?还是不平?我忽然抓起咖啡馆的菜单,像打动物那样去打润明,接着我又用咖啡泼他,上前去撕他的衣服,咬他,踢他,我失去了一个淑女的风度,像野兽一样把怨气一股脑地化为了暴力。咖啡馆的人一下子呆住了,一时之间,他们忘记来拉我,一任我疯狂地用武力去对付那个辜负我的男人。我一边打一边大哭,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号啕大哭。
眼泪洗刷了我,润明走后,许久许久,我呆在咖啡馆里,没有动。
有一位侍者小心翼翼地上前替我续了杯咖啡,她迟疑了半天,终于轻轻地对我说:“小姐,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生这么大的气,书上都说,当你不再爱一个人,你应该云淡风清地看待一切。”
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,但是,所谓的道理,都是说给理智的人听的,而一个女人,在被男人抛弃和背叛的时候,她最想做的只是:打死他。
我遵从了一次自己的情感,在台北的咖啡屋变成了一个女野人,但我不后悔,因为这件事情是在证明:我活着。
我在有血有肉地活着;有感觉、有痛楚地活着。有仇报仇有怨必发地活着。
四年以后,我来到日本,成为了一名图书管理员。我还是像从前一样,过着规律清淡,按部就班的生活。像别人看到的那样,我是一个沉默、文静、害羞、不善言辞的小女子,他们也许觉得有这样外表的女子,应该是逆来顺受,对生活从无反对意见,并且相当柔弱的人。但是,他们不知道,我内心有火,手中有力量,如果再次遇到伤害我的人,我还会大力的吼出来:“我打死你,快给我滚开!”
我不是纸板上的蝴蝶,我没有自我麻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