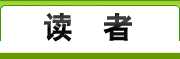维也纳金色大厅里,宋飞轻运弓弦,顿挫有节的旋律立时从二胡中婉转悠扬地流淌出来:一会儿,她带着人们走出空山幽谷,那《空山鸟语》在她的弓弦上生气盎然、百鸟鸣啭,简直令人流连忘返;然后她又带着我们去了瞎子阿炳的故乡,饱尝人间辛酸的《二泉映月》——与我们一样,金发碧眼的“洋人”们也动容了……
音乐真的能够让她在很多人面前飞起来
仿佛命中注定,宋飞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学二胡的。
宋飞的父亲是天津音乐学院的二胡教授,母亲是电台的音乐编辑。很小的时候,宋飞就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学琴,因为她住在音乐学院的家属楼,因为家属楼里几乎每一个孩子到了年龄都要学音乐、学琴。
爸爸教学生的时候,她常扒在琴房外面听,她觉得好奇,怎么手指放在那个大玩具上,就能有这么好听的调子呢?等他们走了以后,她一定得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东西,她想。她走了进去,抱起二胡,“吱嘎吱嘎”地试,因为会唱歌,她就在弦上找自己熟悉的音符。那一年,她5岁。
有一天,她跟爸爸说:快来呀,快来听我拉琴,你不教,我也会拉琴啦。她就拉给他听。爸爸很高兴,觉得她有这方面的悟性。然后是他教了她第一首曲子《找朋友》。小朋友们都会唱:“找啊找啊找朋友,找到一个好朋友,敬个礼,握握手,你是我的好朋友。”爸爸在二胡上拉,她就觉得太有意思了,别人都是用嘴唱,而她不用张嘴,就可以把这些歌唱出来啦。
开始教她“哆”“来”“咪”“发”“索”“拉”“西”时,爸爸就说:“兜来米”就是兜来一兜子米,放时间长了,发潮了,就发了,发了不就馊了,馊了吃了就拉了稀了。小宋飞记住了。她也表现出了自己的主动性,除了爸爸教她的之外,她自己翻谱子,然后,努力拉给爸爸听。
一旦学琴了,爸爸对小宋飞的要求也格外严了,差一点儿,他都不让她过去。所以宋飞给爸爸起了个外号,叫“宋扒皮”。举个例子,夜深了,一个乐段,她得连着拉五遍对的(父亲满意的),拉完后,她以为就可以休息了,可是,爸爸说,接着往下拉。一个男孩子正巧碰见了,说:我要是你哥哥,就带你看电影去。那一次,她的眼泪“唰”地就流下来了。还有一次,小朋友来找她玩儿,正好碰上爸爸给她出了一个乐段,比较难背的那几句,反反复复,差不多拉了四个小时了,一直没停。小朋友就蹲在门外的窗帘下等她,不走。她也是拉一弓,看一下表,再拉一弓,再看一下表。天很热,宋飞很小,而爸爸似乎是忘记了这一点,他一遍又一遍地作着示范,直到最后,她拉的符合他的要求了,才结束。
7岁的孩子能做什么?能帮妈妈洗衣服?能写100个汉字?宋飞不知道,她只知道,她7岁时,能拉刘天华的《空山鸟语》,还有,比如,《赛马》之类的曲子了。这一年,爸爸就带她去参加少儿文艺汇演。在舞台上与平常练琴时的感受不一样,她记得很清楚,她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,台下坐着1000多人,她有些肝儿颤了,她试了试琴,弦也不太准。她想,算了吧,下去吧,她真的就跑了下来。爸爸正在侧台,她跟爸爸说:不准,也不敢拉。爸爸调了调弦,说:没事儿,去吧,像飞起来一样去吧。那一天,她拉的曲子是《云雀》,那种感觉,她回忆,音乐真的能够让她在很多人面前飞起来。
直到大学毕业,宋飞都是个不爱说话的姑娘。一是因为,她常跟大人一块儿演出,很少有机会和同龄的孩子交流;二来也因为,在她上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的那六年里,她下了课就回家照顾那时候瘫痪在床上的妈妈。
她儿时的玩伴说:“印象中很深呢,有一次,她穿着不知道是她妈妈还是她姐姐的高跟鞋,跟所有爱美的小姑娘一样,出来跟我们玩。玩着玩着,她突然想起来了:哎呀,不行,我得回家给我妈做饭去了。当时她家住在学校里,我经常看见她出来买菜,然后回家做饭,有时候,还看见她扶着有病的妈妈,到操场里面转一转。”
那时候,不像现在有暖气,每到冬天,她还得把煤球往三楼的家里搬。五六百斤煤,一个小姑娘怎么搬得动?你猜怎么着,她会发动群众,她把她们班的同学都给叫来,搬完了,码好了,同学们却弄得满脸满身都是黑。想起这件事儿来,直到现在,宋飞的妈妈都觉得特别内疚,特别对不起她。为什么呢,在院子里,小朋友们跳房子,捉迷藏,你追我赶的,而她除了照顾妈妈,就是练琴,就是学习,没有玩耍的机会。
宋飞会做衣服。妈妈瘫痪了以后,因为吃药的原因,妈妈变得很胖。家里的女主人病倒了,衣服就需要宋飞去买。后来,妈妈长得太胖了,买不到了,她就想办法动手给妈妈做,给妈妈织毛衣。不仅这样,她还给自己做演出服,演出、参加比赛,她都穿过,有的衣服现在来看,也还做得不错呢。
小河流入大海了
在天津音乐学院上附中的时候,她就有机会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比赛了,也得过不少银奖、银牌。1985年,她16岁。那一年,北京有个全国二胡邀请赛,这是一场成人间的比赛,在这个比赛中,她像初生的牛犊一样,得了二等奖,还得了一个规定曲目的最佳演奏奖。当时的比赛是关着幕的,评委看不见选手,观众看得见。当她最后一个拉完《听松》时,评委们都说她的《听松》好,但决不相信是一个16岁的孩子拉的,因为她的音乐传达给人们的是男孩儿、大人的、成熟的气质。
爸爸对她太苛刻了。有一次,她跟爸爸急了,冲着爸爸就说:我不跟你学了,也不得那个奖了,在别人眼里,我已经很不错了,你却天天把我说得一无是处!我干吗非跟你学!别人不跟你学也能得一等奖。爸爸笑了,说:你也挺好的,不过,我就是爱在鸡蛋里挑点骨头,我给你挑干净了,别人不就挑不着了吗?是的,每到比赛前,不仅是爸爸一个人挑,爸爸是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主任,他把所有教二胡的老师都集合起来,一轮一轮地,“围剿”她,围剿他们几个选手,然后,挑他们的“毛病”。那一次,参加比赛前,她在大礼堂里拉《长城随想》,舞台空荡荡的,没有人。拉完后,她跟爸爸说:我今天有了那种站在长城上,成为一个伟人的感受了。爸爸笑了。
1987年,宋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。刚来北京读书的时候,她有些失落,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。不是吗?换一个人,比如,你在天津,在父母的周围,你像一颗明珠,突然换了一个地方,或者说小河流入大海了,你显得平常了,你也会有这种心理落差。宋飞向学校提出申请,希望再学一个古琴专业,学校就去中央音乐学院为她请老师。渐渐地,她找到了新生活的感觉。古琴,她也学得很快,到最后,二胡、古琴成了她的双主科了。
在学校期间,她参加了两次重大的比赛,一次是电视大奖赛,她获得了二等奖;另一次是1989年6月的首届“ART”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,她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。那时她正上大学二年级。得了一等奖后,她又进入了刚上大学时的那种茫然的状态。在此之前的全国比赛中,她获得的都是二等奖,有一次,她跟爸爸开玩笑,说:我得不了“三连冠”,我能得“三连亚”。可是,现在得了冠军了,到了高峰了,前面的无数条路该往哪里走?
这时候,她的老师安如砺建议她再跟刘明源老师学琴。刘老师出身民间,与学院派老师的音乐状态和教学状态不同,而且,他不只是会二胡,板胡、高胡、中胡、京胡等民族拉弦乐器,他都会。对于宋飞来说,一下子,又找到了更多的乐趣。刘老师年纪大了,所以,每次上课都要到月坛北街老师的家里去。从中国音乐学院到月坛北街,骑自行车,快一些的话,需要一个小时。男生懒,都起不来床,所以,早上的第一堂课总是她去上。去老师家时,正赶上早晨上班的高峰,这么多把琴,她夹在车上、背在身上,跟装备车似的出发了,碰到下雨下雪就要辛苦多了。
刘明源老师像一锅陈年老汤,让宋飞怎么品都觉得他无穷无尽。他也特别风趣,举个例子吧,他是天津人,吃饭讲究,早饭总是焦圈儿啊、炒肝儿啊,等等,不同的口味儿。每天早晨,见到宋飞,他总是问:吃饭了没有?宋飞回答:我不饿。他又总是说:吃饭是个人卫生,要讲卫生。有的时候,他也给宋飞打电话:哎,儿子(他叫她儿子,就因为喜欢她拉琴时像男孩子的那股劲儿)别忘了,来的时候,带一斤烧饼来。宋飞问:咱吃涮羊肉啊?他回答:多俗气啊,咱吃羊杂碎。
跟他学琴,宋飞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他拉琴不固定演奏,不固定手法,他的音乐永远是活的,就像咱说话似的,前面重读了,后面就要轻读,前面的忽略了,后面的就要强调。从他那里,宋飞学会了用无数种方法去表达同样的一种感受。这跟用固定的手法拉十遍,十遍都一样的完美不一样,它是一种高级的状态。从此之后,宋飞不再固定自己的演奏技法,一直到现在。
寻找到音乐的本质
宋飞似乎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攀登者。
大学的后两年,她又拜了天津的古琴名家张子谦先生为师。张先生收她做他的关门弟子。每两个星期,她都背着琴,坐着火车,到天津上课去。师从张先生,让她有了另一种不同的感受。她跟他学琴的时候,他已经90多岁了,手指不灵活,耳朵也背了。不是吗?他的音乐的节奏、音准可能不是最完美的,而我,宋飞想,即使是演奏得再准确,也不如他,为什么?音乐中还有什么更重要的,她没有发现?后来,她注意到,张先生只要往那儿一坐,就已经把大家的心抓走了,她也才知道,她天天练的、想要达到的完美、精确的那些东西,只是一层外衣,她还要寻找到音乐的本质。
有一次,她又得了第一名,电视台要拍一个她跟张先生上课的片段。那一天,阳光太强了,拍一会儿,就得等光弱一些再拍。她就对张先生说:我扶您去树阴底下坐会儿吧,晒得太难受了。张先生说:我不要紧,我的琴不能晒,把它抱过去吧。音乐的本质是什么?老一代的艺术家,他们把音乐注入他们的生命,然后音乐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,宋飞想,所以,他们的音乐才那么的珍贵——像瞎子阿炳的音乐,像刘天华的音乐。
自从宋飞的二胡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奏响后,国人高兴啊,大家奔走相告:我们的民族音乐被关注了。可宋飞不这么认为,她觉得,这只是一种强心针的状态,不等于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活过来了。
她常有演出,来的观众很多,但她发现,观众们未必都能够懂得她的音乐,或者说他们对她的音乐的理解有偏差。而她左右不了他们。他们可能特别高兴,特别高兴见到了她,跟她照张像,让她签个字,然后是赞美她不以为好的地方,那个时候,她心里的那个失落,无法用语言表达。
所以,她选择了回国——回到她的母校中国音乐学院做一名教师。学校的空间虽然很小,但是,她可以通过传授文化上的信息和理念去打开学生的思想空间。她要教他们的是如何与音乐为伴,如何用音乐装点心灵,不是吗?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世界,世界立刻就变得与众不同了。这就是音乐的力量。
在教学的过程中,实际上她是采用了一种双语的模式,即用母语和外来语两种文化元素同时给音乐的高楼大厦添砖加瓦。也就是说,有的时候,音乐需要用非常母语化的表达去诠释;而另外一些时候,比方说,用二胡去演奏西方的乐曲,这时候,就需要我们像尊重自己的传统一样尊重别人的传统了。她用了一个形容的比喻说,这种双语的模式就像双腿走路,瘸了哪一条腿都不行。再进一步说吧,音乐就像一栋房子,在他们小的时候,她就得告诉他们:这里面有多少房间,每个房间里有什么风景;长大了之后,他们才能知道,哪个房间是值得他流连忘返的,哪个房间是需要他浏览的——渐渐的,他的内心变得丰富多采了、变得博大了,然后呢,我们的民族音乐就不愁活不过来。她坚信。
那一天,在飞机上,她看到了一篇画家的文章,画家说: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,或多或少地会感觉到我们似乎是站在了文化断层的边缘。她也有同样的感觉——为了不丢掉这个根,需要去寻找那个断层,把民族的文化接续上,然后,才能接着前行。所以,她回过头去——当然,前面已经讲过,她并不是国粹主义,许多西洋的东西、现代的东西,她也能拉,但是,拉这些曲子的时候,她注重作品的情、意、趣,她让它们既不失传统的韵味,也让它们同时带有时代的个性。前些时候,她以胡琴、古琴、琵琶等十三种弦乐器举办了一场颇具特色的“弦索十三弄”独奏音乐会,这实际上就是她站在文化断层的边缘,为民族音乐做着她能够做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