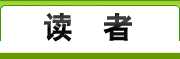法默(1915-1970),美国女影星,早年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戏剧系。1935年去百老汇演戏,不久入好莱坞,1940年代前半期曾红极一时。1945年,正当法默在影坛如日高升之时,却因不愿听人摆布、随波逐流而遭到无情打击,她被诬有精神病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达8年之久……
我曾被关在州立精神病院里,和疯子在一起住了8年。在那些年月里,我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恐怖,蜕变成了一个像野生动物似的胆战心惊、只图苟延残喘的小生命。
但是,我活下来了。
我曾被精神病院的男看护轮奸过,被老鼠啃咬过,还曾因为吃腐烂食物而中毒。
但是,我活下来了。
我曾被锁在墙上装有软垫的疯人禁闭室里,上了镣铐,身穿约束衣,半浸在冰水里。
但是,我活下来了。
精神病院本身就是一个铁笼子。我并不是活着出来的胜利者,而是战战兢兢地爬出来的失败者,伤痕累累,孤独悲伤。
但是,我活下来了。
同疯子生活在一起的3040天,留下了永难愈合的精神创伤,伤口至今仍在发炎、化脓。我深深地感到,幸存的人没有胜利可言,有的只是悲伤。
我仍能回忆起最终把我送入绝境的种种纷乱的景况,但我始终理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所留下的只是痛苦的回忆;这一切确实都发生了,而我也终于活下来了。
我的一生中从未曾有过愉快的回忆,因为我降生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。在我父母的生活中,我降生得太晚了,他们在长时间的激烈争吵后,总要把我当作最后发泄的对象。童年是一段充满渴望的年代,但是,我的童年却从未享受过爱抚,甚至从未感到有谁需要我,我也不记得受过什么保护。我一生的大多数时光就是在这种孤独中度过的。
那么,谁应当对这种痛苦负责呢?当然,我归咎于自己暴躁的性情,但也有另外一个坏蛋。
我一开始就认为,我不能归罪于上帝。因为在我的心目中,他太遥远了,而且也不会特别把我挑出来,以他万能的力量来对付我。
犹太人有句俗语:“上帝不能无所不在,因此他创造了母亲。”不管我这样做是否公正,我把我母亲视为使我绝望的主要根源。
不管我们进行过多么艰苦的努力,我们母女之间没有一种默契,我们的关系就很紧张,经常争吵。
我的母亲是个意志坚强、武断固执的女人,她的古怪脾气把我逼进可怕的境地,几乎毁掉了我的一生。
不过,从另一方面讲,我也不是个听话的孩子。我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武器尽可能地反抗她。就是这种长期激烈的争斗,最终把我推入了那种凡人所可能遭遇的最可怕的境地。
从21岁到28岁,我拍了19部故事影片,演了3部百老汇戏剧和7部非百老汇戏剧,在30多部广播剧中领衔主演,单独出场则不计其数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在事业上青云直上,但内心却忧虑重重。我心里明白,我一直未能适应好莱坞的压力,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,我是电影界最不受欢迎的明星之一。
我是一个不易相处、爱发脾气的女演员,在上层中树敌不少。记得曾读到过一篇文章,我的一名导演在这篇文章里说:“关于弗朗西丝·法默,我所能说的最好的一点是,她是完全难以忍受的。”他无疑是对的,因为我发现,好莱坞和电影界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。
在我遭受不幸期间,我的婚姻也不欢而散。1943年秋天,我这个易受惊吓、劳碌过度、苦难深重的年轻女子彻底地垮了。
我一生中的悲剧,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———我因为在半灯火管制区亮着灯开车而遭拘捕。从这次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拘留开始,对我的种种起诉接踵而至,滚雪球似地演成了一场全国性丑闻。我因此被判刑半年,监外执行,由于我没有按要求向假释官定期汇报我的活动,一纸逮捕令又将我召入狱中。
我报之以激烈地反抗,闹了个天翻地覆!最后,法院将我转到电影演员疗养院去“休养”。这样,我至少避免了蹲监狱。在那段软禁期间,如果我能独处一段时间的话,也许还能收拾残局,重整旗鼓。可是我那当律师的父亲却从法院获得许可,把我引渡到家乡华盛顿州,将我置于我母亲的法律监护之下。
我刚回家的时候,虽然我的事业和个人生活已是一败涂地,但我仍希冀着能重拾旧梦。
从被置于母亲的法律保护之下的那一刻起,我就被推入了无法逃脱的万丈深渊。时隔不久,她就把我送进了离家不远的西雅图州立精神病院。我在那儿住了3个月,然后“彻底治愈”出院。不幸的是,我没有解除母亲对我监护权的足够知识,我被与一个似乎决心要毁掉我一生的女人拴在一起,也许她并非完全故意。从医院出来后,我仍在她监护之下。在此后的7年里,她对我的权力和控制是至高无上的。
我无处可去,只好回家和她同住。虽然我的事业和生活已一败涂地,但我仍然想东山再起。可是,在我30岁那年,一切希望皆成泡影。1945年5月22日早晨,我走上了永难回头的绝路。1964年以后的我已达到顶峰。作为一名女演员,我已满意至极。但我一直想知道,以个人演唱掌握观众,将是何种感受。
早已成为我好友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经理卡尔·温纳哈特和他的夫人尼塔建议我为美术馆成员举办一次诗歌晚会。我踌躇不定,但愈想觉得有意思。于是1968年5月,我为该馆听众朗诵了坦尼森的《伊诺克·阿登》和其他诗作,包括我最喜欢的埃米莉·狄金生的《黎明真的会降临吗?》,从中得到的自我满足填补了我的空虚,我知道我的表演渴望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。
我演《贵妇还乡》和朗诵《伊诺克·阿登》,不是为了金钱,而是因为这两个节目艺术上的成就,把这同好莱坞的金钱交易相比,是多么有意思。一个填满了我的钱包,另一个则充实了我的灵魂。我生活中纷繁的头绪似乎在聚拢。我把1968年夏天记作我再生的时节。想到这里,我记起了圣经上的一句话:“……一个小孩子将引导他们。”
直到我同“我的外甥女们”建立起感情以前,我从未接近过孩子。实际上,这一点是我为了避免联想而牢记在心的,因为我对在好莱坞打胎感到罪过。我没有胆量面对孩子,但这5个小女孩打开了我的心扉,驱除了我的罪恶感。
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,法莱尔带她们来游玩,吉恩不停地为她们的饮食和活动操劳,我的大部分时间则用以监视她们游泳,因为我们从不让孩子们失去保护。午后,法莱尔决定她们该走了,她们失望地叫喊起来,她把她们召集到一起,答应她们改日再来。孩子们总是高兴地到来,兴奋地离去,对我似乎也是如此,这一天也不例外。她们不是找毛巾,就是找鞋子,经过一阵混乱,一切收拾停当以后,就消失在屋后,向她们的汽车走去。她们一走,院里顿时一片寂静,因为孩子们来时带来一种音乐般的东西,而她们一走,吉恩就筋疲力尽地但愉快地叹了口气,回屋躺下了。
院子里空荡荡的,我突然感到孤独和忧郁。周围静得可怕,阳光在水面闪耀,几乎使空气中出现了幻景。我无法描绘我的思想,我感到了爱的温暖,突然又领略了出乎意料的孤独的痛苦。我的感情空虚、迷茫,也许可以用情绪忧郁4个字来形容。
就在这时,我看见了“我的外甥女”吉娜,她当时12岁,正站在屋角外腼腆地望着我,然后,一边向我跑来,一边用天真的童音喊着:“弗朗西丝阿姨,我告别时没有吻你。”
我向她伸开双臂,感到她的脸蛋贴在我脸颊上,听见她用蝴蝶飞舞般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说:“我多么爱你,因为你好。”然后,她又一蹦一跳地走了,长长的头发像风中摇曳的花朵在她身后摆动。当她离开时,我胸中发出一声呜咽,从未有人对我这样说过,也许从未有人这样想过。此时此地,因为此事,铁石心肠熔化了。
我不禁泪如泉涌,不是因为有人我说爱我,或说我好,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打动了我的心。
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,我知道包围着我的一切鬼魅正被驱散,我充满了原宥过去和重新开始的力量。
生活有了新的意义,一切都生机勃勃,力量像泉水似地从我身上涌出,我获得了新生。